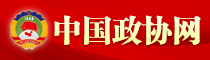瞿杨生
那天,太阳依旧毒辣,电钻和切割机的噪音依旧震耳欲聋。我正蹲在楼板上绑扎钢筋,汗水顺着额头淌下来,流进眼睛里,一阵刺痛。我下意识地闭上眼,想用脏兮兮的衣袖去擦,却又停住了。
就在那一瞬间,一阵风拂过我的后颈。
那不是之前那种裹着热气的、充满侵略性的风。这阵风,竟然带了一丝……凉意。很轻,很柔,像一片羽毛悄悄滑过。它没有驱散酷热,却像在闷热的铁屋子里,突然被推开了一道缝。那一丝凉,瞬间抚平了皮肤上的燥,也安抚了心里头的火。
我猛地睁开眼,看见不远处的老王也停下了手里的活计,他仰着那张被太阳雕刻得沟壑纵横的脸,闭着眼睛,喉结动了一下,像是在品咂什么滋味。
“老王?”我喊了一声。
他没睁眼,嘴却咧开一个缝,憨厚地笑:“风,凉快了。”
就这么一句,像是按下了什么开关。整个工地仿佛都静了一瞬。大家好像都感受到了。有人下意识地松了松安全帽的带子,有人贪婪地多吸了几口气,还有人干脆把湿透的工服前襟扯开,让那带着“凉信儿”的风,直接吹在胸口上。
这阵风,就是处暑的信使。它不像日历上的节气,印在纸上,冷冰冰的。它是活的,有体感的,是老天爷递给我们这些苦熬的汉子们最实在的慰问信。
从那天起,风就一天比一天不同了。它不再那么暴躁,开始有了自己的“性格”。早晨的风,带着点露水的湿润,吹在脸上,是清爽的;傍晚的风,从西边的天际线吹来,带走了最后一丝暑气,也吹长了我们在夕阳下的影子。我们收工时,总会不约而同地多站一会儿,让这变了脾性的风,吹走一身的疲惫。
工地的噪音依旧,灰尘依旧,我们的活计也依旧繁重。但所有人都知道,最难熬的日子,过去了。老王的话也多了起来,开始跟我们聊他老家的那片玉米地,说这个节气,玉米该灌浆了,风吹过玉米林,哗啦啦地响,比城里的任何音乐都好听。
我抬头看看眼前这片正在一天天长高的楼,再看看身边这些被晒得黝黑、却因为一阵风而舒展了眉头的工友们。我想,无论是乡间的玉米地,还是这城市里的钢铁森林,我们都活在同一片天空下,被同样的节气所抚慰。
工地的风,真的凉了。这风里,有秋天的味道,有收工回家的盼头,也有一份苦尽甘来的、微小而确切的慰藉。
- 第 1 版: 要闻 孙大伟走访慰问抗战将领遗属
- 第 2 版: 精选 “戒网瘾”机构,能拯救网瘾少年吗?
- 第 3 版: 关注 编造“人设”引流 动辄数万“入会费”——一些婚恋机构“爱情买卖”调查
- 第 4 版: 导读 期待九三阅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