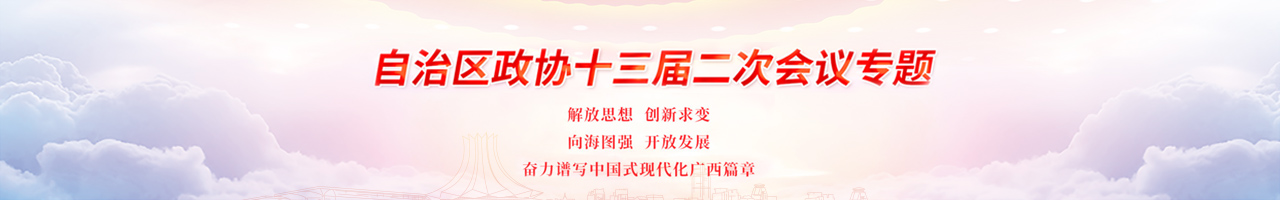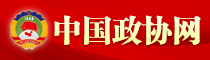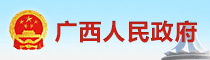黄 颖
说到美食,人们最初想到的往往是能登大雅之堂的,比如曹雪芹笔下的那些珍馐,那才是真正“有身价”的。大观园里的太太小姐们的嘴还真是刁钻,高贵的食物自然会是美味。
但难能可贵的是,穷人家也可以把那些“不登大雅之堂”的食物吃出滋味来。一位叫姜淑梅的老太太写了一本书,名为《穷时候,乱时候》。她生在饥荒年代,二月天,青黄不接,便去摘各类野菜,说是“榆树叶子最好吃”。这榆钱儿好吃,在刘绍棠的《榆钱饭》里就早已领略过:
“小时候,年年青黄不接春三月,榆钱儿就是穷苦人的救命粮。”“九成榆钱儿搅合一成玉米面,上屉锅里蒸,水一开花就算熟,只填一灶柴火就够火候儿。然后,盛进碗里,把切碎的碧绿白嫩的春葱,泡上隔年的老腌汤,拌在榆钱饭里;吃着很顺口,也能哄饱肚皮。”
榆钱儿能吃,榆树皮也是美味。姜老太太提到:“把地瓜干放到石头囤窑子里砸碎,把干榆树皮碾碎放到磨上,磨成面,两样放在一起做粥,又黏又滑,很好吃。”
看到这里,不禁也流下口水。
网上有人发文,说几个出国留学生搭伙做饭,一次特馋饺子,没想到满大街找不到卖韭菜的,只有卖大葱的——可大葱包饺子怎会香呢?不知谁发现某家屋后长着无人问津的荠菜。几人商量好了,等主人不在家,偷偷跨过竹篱笆去“偷”。没想到主人突然回来,大家逃散不及。被问起来,主人惊呼:“这野草也能吃?”
主人没有怪罪,甚至有些巴不得——有人免费为自家除“草”,何乐而不为?
留学生美美地吃了顿荠菜饺子,也不忘给荠菜的主人送去一些。主人吃后连连赞叹,自家有这样的“美食”,以前怎么会不知道呢。
白皮肤蓝眼睛的他们怎会知道,读小学的时候,我们就已经晓得这“荠菜”是种美味了。小学课本里,张洁把荠菜写得极美:“田野里长满了各种野菜:……最好吃的是荠菜。把它下在玉米糊糊里,再放上点盐花,真是无上的美味啊!”
最近特馋“地瓜粉团”。酒店里倒也做,但总觉得不是那个滋味。做此菜最拿手的是老家的大娘,70多岁的老人做起这道菜依然有模有样。早前地瓜从地里收上来,磨成浆、晒成粉,可以吃上一季。做的时候下足地瓜粉,加以虾米、花菜、萝卜丝、五花肉,加热水捏成团。待锅里的水煮开,把捏好的粉团一个个下到水里,然后就等着它们从锅底浮上来——这就做好了。
大娘感叹说,这地瓜也不是什么金贵的东西,比不上大米白面,当年是穷人家的主要粮食。饥荒年代地瓜好养活,比大米白面更不娇贵,更能填饱肚子。如今日子好了,吃的人却少了。
谁想,如今这地瓜摇身一变,竟成了酒家食肆里能够堂而皇之上桌的一道菜。其实就如生活一样,奢侈的不见得是好的,锦衣玉食不一定能比得上粗茶淡饭。能够慰藉人心的,才是最好的。
- 第 1 版: 要闻 孙大伟走访慰问抗战将领遗属
- 第 2 版: 精选 “戒网瘾”机构,能拯救网瘾少年吗?
- 第 3 版: 关注 编造“人设”引流 动辄数万“入会费”——一些婚恋机构“爱情买卖”调查
- 第 4 版: 导读 期待九三阅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