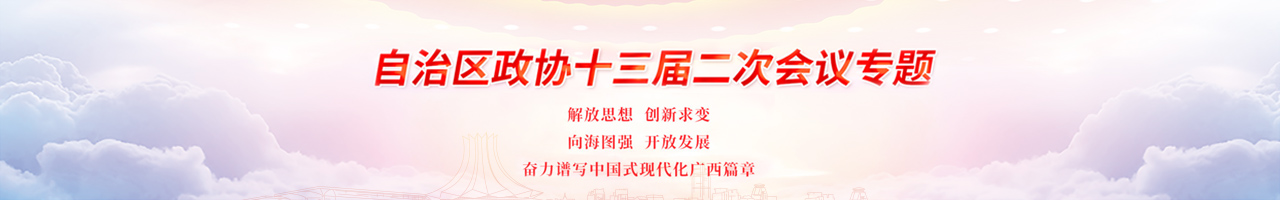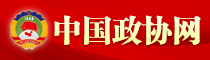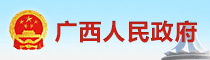烽火尽处的民族之声
——名家笔下的抗战胜利描写
俞继东
1945年8月15日,正午的重庆酷热难当。周而复在《长城万里图》中记录下这历史性的一刻:广播中传来日本天皇宣读终战诏书的异样声音,字句虽模糊,其意却如惊雷。刹那间,“整个山城在沸腾!”人们涌上街头,拥抱、跳跃,眼泪与欢笑交织。
而巴金在《寒夜》中捕捉了市井的欢腾细节:“街上人如潮涌,一片狂欢景象”,“号外!号外!”的喊声此起彼伏,报童穿梭于人群之中,将印着巨大喜讯的薄薄纸张递到一双双颤抖的手上。这一日,整个民族如卸下了万钧重担,在喜极而泣中重获新生。
同一时刻,数千里外的北平,却经历着一种别样而深沉的喜悦。沦陷区的人们,在八年暗夜里挣扎求生,此刻终于盼到了云开雾散。老舍在《四世同堂》结尾处,以祁老太爷一家为缩影,描绘了北平人心灵的复苏。当胜利的消息如微风般拂过胡同深处,祁老太爷枯寂的心底忽然焕发出久违的生机:“他的心跳得很快。他不再迟疑,拿着钱就走出门去。”他走到街上,怀着一种近乎朝圣的心情,买回了一面小小的国旗,这面在沦陷岁月中只能深藏心底的旗帜,此刻终于可以重新沐浴在自由的阳光下了。祁老太爷“郑重其事地把它挂在门楣上”,那旗帜,不仅宣告着一个旧时代的终结,更是一个古老民族在屈辱的灰烬中重新挺立的象征。当第一阵胜利的爆竹声在北平寂静多年的街巷中猝然炸响,人们“先是惊疑不定,继而恍然彻悟”,那声音如春雷唤醒冻土,无数紧闭的门扉次第打开,无数张饱经风霜的脸上,泪水与笑容同时绽放。
胜利的火焰,亦以不同姿态燃烧在神州各处。在革命圣地延安,丁玲以朴素而热烈的笔触描绘出边区人民的情感喷涌。当胜利的电波翻越千山万壑抵达黄土高原,整个延安城瞬间被点燃。丁玲在《延安集》中写道:“胜利的消息传来,延安沸腾了!”刹那间,锣鼓喧天,彩旗如林,军民自发地涌向街头,扭起酣畅淋漓的秧歌。那奔放有力的舞步,是压抑多年的狂喜在黄土地上最质朴的释放,每一记鼓点都敲击着解放的心声。在简陋却充满生机的窑洞前,在飞扬的尘土与震天的口号声中,一种新生的力量正蓬勃生长。
在南国艰辛的流亡途中,丰子恺则以他特有的悲悯与静观,记录下胜利消息猝然降临时那令人心颤的瞬间。他在《胜利之夜》中回忆,当“日本投降”的喜讯如天外飞鸿般传到流徙的人群中,他正肩负箩筐艰难前行。这石破天惊的消息使他双手一松,“箩筐从肩上翻落在地”。这并非疏忽,是巨大的喜悦骤然压垮了长久紧绷的神经。紧接着,四面八方响起了鞭炮声,噼啪作响,驱散了流亡路上的阴霾与悲苦。丰子恺在文中慨然写道:“这鞭炮声驱散了八年的阴霾,照亮了流亡者归家的路。”
在西南联大的象牙塔内,胜利的喜讯同样激荡着学子的心。汪曾祺后来在《跑警报》等散文中,虽未直写胜利日,却精准捕捉了那个特殊时代的知识分子情态。消息传来时,联大师生们“先是静默,继而掌声雷动”,那份静默,是对漫长苦难岁月的无声告别;那雷动的掌声,则是对浴火重生之未来的无限憧憬。年轻的学子们跑出教室,奔向街头,与昆明市民共同欢呼,将书本中的家国情怀瞬间化为眼前的真实热流。
从重庆沸腾的街市到北平悄然悬挂的国旗,从延安震天的锣鼓到流亡路上翻倒的箩筐,1945年的夏天,整个中国被一种巨大的情感所席卷。无数个体用泪水、欢呼与静默,共同谱写了这部荡气回肠的《胜利交响曲》。而历史深处的箴言早已刻写:胜利并非苦难的终结,而是一个民族带着伤痕与记忆,在坚韧中重新出发的起点。在民族记忆的长河中,胜利之日不仅是历史的刻度,更是民族魂魄在血火中淬炼、于坚韧中重铸的不朽坐标。
- 第 1 版: 要闻 “两山”理念改变中国引领时代
- 第 2 版: 精选 “两山”理念改变中国引领时代
- 第 3 版: 关注 侵华日军细菌战暴行再添铁证
- 第 4 版: 导读 烽火尽处的民族之声——名家笔下的抗战胜利描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