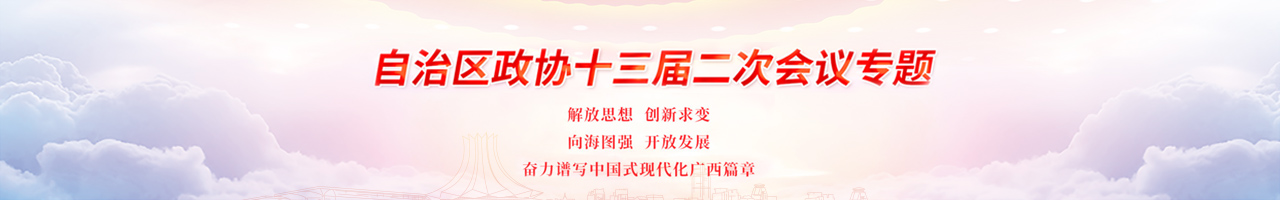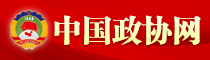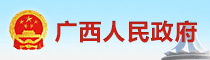钱续坤
读茅盾先生的散文《风景谈》,感触最深的便是:只要你有一双善于发现美的眼睛,风景无处不有,无时不在。吾虽天生驽钝,却对大千世界充满好奇之心,譬如流星会吸引我不眨眼睛,譬如流萤会诱惑我步履轻盈。
不眨眼睛,专注的自然是星空的好奇神秘;步履轻盈,关注的则是那忽明忽暗的灵动身影。当然,这背景的选择肯定是在孩提时代夏秋时节的夜晚。那时乡村的文化生活极其贫瘠,晚饭之后最大的乐趣便是到晒场上纳凉,要么听些狐仙鬼怪的故事,要么玩些孩童的游戏。顽皮好动是孩子们的天性,晒场四周那黑魆魆的田野,便是他们尽情嬉戏的“乐园”,其中饶有趣味的,当属手提玻璃做的罐头瓶,蹑手蹑脚地走到草丛中,去寻找那闪着白光的萤火虫。孩子们不费吹灰之力,就能使那玻璃瓶变得闪烁起来,然后他们再乐此不疲地把玩半天,直至夜深人静带回家中,挂在蚊帐里面任其自闪自灭。
小时候的我觉得自己俨然就是一位颇有造诣的画家,黝黑深邃的夜幕就是我的画板,废旧蚊帐做成的网兜就是我的画笔,颜料呢,始终只有一种色彩,肯定是萤火虫尾部发出的银光。平视,只见“画笔”一点一点地滑动,连点成线,仿佛一条流动的溪水,虽无声,却优美;仰望,惊叹如此之多的“流萤”在星空向你眨巴着眼睛,诱惑你想象“嫦娥奔月”与“吴刚伐桂”的神话传说;低头,平静的池塘里波光粼粼,倒有点“乱花渐欲迷人眼”的况味……每天置身于如此美轮美奂的意境,小小的画家尽管难以泼洒出气吞山河的鸿篇巨制,倒也可以勾勒些恬淡随意的山水小品,岂不快哉!乐哉!美哉!
视觉的快慰并不能满足童年的欲望,因为想当画家的梦想只是个体的行为,如果不融入到集体之中去,要么离群寡居,要么保守自闭,完全体验不到同伴之间嬉闹玩乐的莫大情趣。其时还有一件美事至今令人回味无穷:比唱有关萤火虫的儿歌。比赛的场地依然是在纳凉的晒场上,比赛的选手则男女不限,由各家推选一名孩子参与;这时真正较量的并不是懵懂的孩子,而是孩子身后的“教练”与“高参”——母亲与祖母。“萤火虫,夜夜红,提着太阳当灯笼,公公挑担卖胡葱,婆婆养蚕摇丝筒,男儿读书做郎中,女儿织布当裁缝”,“萤火虫,慢慢飞,夏夜里,风轻吹,怕黑的孩子安心睡”……这些脍炙人口的谣曲虽质朴无华却意蕴深远,至少在我幼小的心灵中播下了诗歌启蒙的种子,为我后来爱上文学开启了一扇智慧的“天窗”。
其实萤火虫亦颇受诗人青睐。《诗经·东山》中就有“町疃鹿场,熠耀宵行”的诗句,这“宵行”指的就是萤火虫;杜牧的“红烛秋光冷画屏,轻罗小扇扑流萤”一句,传神得叫人浮想联翩;而最为形象的当属南朝萧纲的《咏萤诗》:“本将秋草并,今与夕风轻。腾空类星陨,拂树若生花。屏疑神火照,帘似夜珠明。逢君拾光彩,不吝此生轻。”此诗通过“类星陨”“若生花”“疑神火”“似夜珠”一连四个比喻,把萤火虫的异常光彩鲜明地表现出来,并以此托物寓意,采用拟人手法,表示只要遇到知音,便要不惜一切,奉献出微薄的力量。
“老翁也学痴儿女,扑得流萤露湿衣。”在这样的夜晚,我依然痴迷于点点流萤在空中,无忧无虑地跳着舞,宠辱不惊地漫着步。那绚丽的舞蹈,那优美的曲线,使我在瞬间突然顿悟:自己也应该像萤火虫那样,提着生命的灯笼,努力照耀着自身能够看见的世界!
- 第 1 版: 要闻 “两山”理念改变中国引领时代
- 第 2 版: 精选 “两山”理念改变中国引领时代
- 第 3 版: 关注 侵华日军细菌战暴行再添铁证
- 第 4 版: 导读 烽火尽处的民族之声——名家笔下的抗战胜利描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