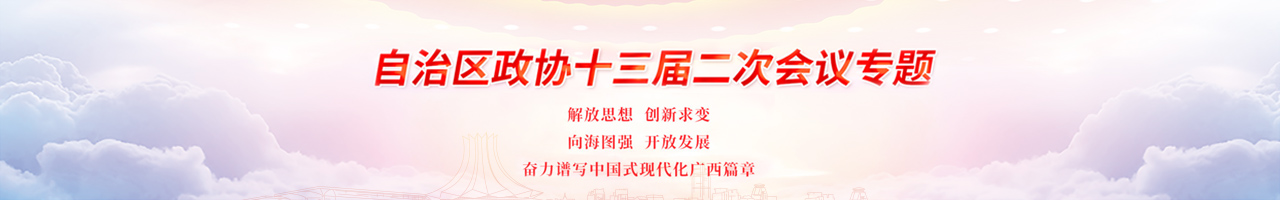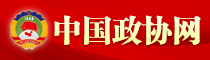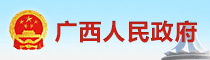邵俊强
小时候见了豆腐,跟见了中药似的,筷子都绕着走。那股子说不清道不明的豆腥味,混着滑溜溜的触感,一沾嘴就直犯恶心,仿佛嘴里闯进了块不请自来的嫩肥肉,还带着股子庄稼地的土气。母亲总说:“豆腐是好东西,养人。”我偏不买账,心想世上吃食千千万,何苦跟这软趴趴的玩意儿较劲?于是好些年里,对豆腐都是敬而远之,桌上有它,我就专攻咸菜和米饭,井水不犯河水。
谁承想风水轮流转,不知哪年夏天,竟栽在了凉拌豆腐手里。那日天热得邪乎,太阳把柏油路晒得能煎鸡蛋,厨房更是像个蒸笼。母亲从凉水里拎出块嫩豆腐,“啪”地扣在粗瓷碗里,用筷子搅碎,然后,滴了点香油,淋了勺生抽,撒了把葱花,说:“对付吃口,凉快。”我本想摇头,可眼瞅着那白绿相间的模样,又实在懒得跟热空气较劲,夹了一块往嘴里送——就这一下,前半生对豆腐的偏见,跟豆腐块似的,碎了。
后来才知道,这不起眼的豆腐,竟是两千多年的老古董。淮南王刘安炼仙丹没炼成,倒炼出了这“植物肉”,说起来也算科技史上最著名的“实验事故”。古人对它的感情深着呢,说它“无骨无筋,有皮有肉”,这话妙极了,你看它软乎乎的没个正形,偏能经得起折腾,煎炒烹炸样样来得,跟市井里那些看着不起眼、实则有真本事的人一个脾气。“煮豆作乳脂为酥,高烧油烛斟蜜酒。”苏东坡将豆腐比作“乳脂”,赞其口感细腻如酥,同时以“蜜酒”相佐,展现了文人雅士的生活情趣。
梁实秋先生写吃,讲究“味在淡中求”,凉拌豆腐算是把这话悟透了。它不像红烧肉那样张牙舞爪地抢风头,也不似鱼翅海参那般端着架子,就那么安安分分地待在盘里,却能把调料的香、豆子的鲜,揉得恰到好处。有次在北京后海那边一条胡同里的老饭馆吃饭,邻桌大爷拌豆腐,非得用自己带的虾油,说“这玩意儿跟豆腐是亲家,少了它,就像唱戏没了弦子”。他一边拌一边念叨:“古人说‘一轮磨上流琼液,百沸汤中滚雪花’,那是磨豆浆的景,咱这拌豆腐,得叫‘一勺生抽融玉色,半滴香油透心凉’。”说得兴起,还真就着豆腐喝了半瓶二锅头,看得我直乐——原来吃口豆腐,也能吃出这般豪情。
刘震云写《一句顶一万句》,说人活着,就图个“说得着”。我看豆腐也是这样,跟谁都“说得着”。配咸菜,它能衬得咸菜不那么齁;就白粥,它能让粥香多几分绵密;哪怕就着剩馒头,也能把干巴巴的馍馍变得有滋有味。有年冬天感冒,没胃口,弄盘凉拌豆腐,只搁了点米醋和蒜末,酸溜溜的,竟把堵在嗓子眼里的腻歪劲儿全冲散了。那一刻忽然懂了,为啥古人写豆腐“软比牛酥便老齿,甜于蜂蜜润枯肠。”,不是夸张,是真到了那份上,它就是最好的解语花。
如今再看豆腐,早没了小时候的嫌弃。菜市场里挑豆腐,总爱选那种用布包着的老豆腐,摸着紧实,闻着有淡淡的豆香。回家做凉拌,也有了自己的讲究:生抽得是晒足了日子的,香油要现磨的芝麻榨的,葱花得是刚从阳台掐的,还得撒把炸得金黄的黄豆,咔嚓一响,脆生生的,像是给豆腐的清唱加了段快板。
从拒之千里到奉为上宾,原来人对吃食的态度,也是对生活的态度。小时候嫌它寡淡,是不懂平淡里的真味;如今爱它清爽,是明白了日子里的从容。就像这凉拌豆腐,不用费尽心机,不用浓油赤酱,简简单单,反而最能让人咂摸出生活的本真——毕竟,能把平凡的日子过出滋味,才是真本事。
- 第 1 版: 要闻 “两山”理念改变中国引领时代
- 第 2 版: 精选 “两山”理念改变中国引领时代
- 第 3 版: 关注 侵华日军细菌战暴行再添铁证
- 第 4 版: 导读 烽火尽处的民族之声——名家笔下的抗战胜利描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