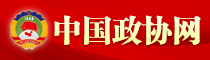彭 晃
霜是夜里悄悄来的。清晨推门,满眼的白。菜畦里,芥菜的叶子上,白菜的帮子上,都敷着一层晶亮的霜衣。
这时,我家屋后那两棵柿子树,便成了最风光的景致。夏日里那团团浓绿、密密匝匝的阔叶,早已被秋风扫尽,只剩下铁画银钩般的枝桠,疏疏朗朗地刺向高远的青空。就在这看似枯寂的枝头,却缀满了一个个小红灯笼似的果实,经了深秋的寒,又经了这几场霜,那颜色不再是初熟时温吞的橙黄,而是一种沉甸甸的深红,红得厚实透亮,衬着青灰的枝条和瓦蓝的天,有种惊心动魄的美。
祖母常说:“柿子不经霜,甜得没骨头。”这话我小时候是不懂的。那时嘴馋,柿子刚转黄,就猴急地去摘,软的就吮,硬的便在米缸里捂着。那甜也是甜的,却总带着一股生涩感。非得等到入了冬,几场霜打过,你再去看那柿子,皮儿仿佛更薄了,隐隐透出蜜一样的瓤。轻轻摘一个,撕开一个小口,那橙红晶莹的果肉,便颤巍巍地漾出来,像封存了一秋的阳光,此刻都化作了稠浆。低头一吮,冰凉浓醇的甜直冲脑门。甜过后,舌尖还留着一种清凛的香。那便是霜的滋味。霜的冷,抽走果实里最后一丝浮躁的水汽与青涩,逼着它将所有的精华与糖分,都沉淀下来,成就了这经得起咂摸的甜美。
我看着手中这枚深红的柿子,忽然觉得,这“经霜”二字,又何止是说果子呢。
想起我的一位忘年交,退休的老程先生。他一生坎坷,人到中年又大病一场,可他如今,却是我们这群人里最静气、也最“有味”的一个。他写字,画画,侍弄满院的花草。他泡的茶格外好喝,他说的故事格外动人。不是因为他技艺多么超群,而是他做一切事情,都有一种不慌不忙、将滋味彻底熬出来的耐心与通透。有一回与他闲聊,他说:“人啊,跟这树上的柿子也差不多。非得经历些寒霜苦楚,把心里那些浮躁的东西都冻一冻,剩下的,才是真东西,才有真滋味。”他说这话时,眼神平和,闪着温润的光。他那份从容与甘冽,不正是岁月与风霜共同“酿”出来的么?
人生一世,草木一秋。谁不盼着风和日暖,顺水行舟?可那似乎只是理想中的童话。更多时候,我们总不免要遇上自己的“霜降”时节——可能是事业的困顿,可能是情感的创痛,可能是健康的警钟,也可能是生命里那些无法言说的虚无与孤独。它们像寒夜的霜,覆盖我们原本绿意盈盈的心田,带来刺骨的冷与荒芜的白。
然而,或许生命的神奇就在于此。霜,不止是肃杀,它更是一种提炼与馈赠。它用极致的冷,逼着我们向内收缩,去凝结那些生命中真正重要的、无法被剥夺的糖分——比如坚韧,比如豁达,比如对寻常日子的珍重,比如穿透表象看清本质的智慧。那些未曾“经霜”的顺遂与甜美,固然可喜,却往往失之浅薄;唯有领教过寒夜的滋味,将那冷意丝丝缕缕地吸收、转化,最终渗入生命的肌理,我们才能收获一种更为深沉醇厚、也更耐得住时光品咂的“回甘”。
窗外的阳光渐渐有了温度,枝头的霜开始化作晶莹的水滴。我慢慢吮尽最后一口柿子的甜,那清凛的余味还在舌间盘旋。忽然觉得,这个冬天,因这“经霜”的觉悟,竟不再那么难挨。生活予我以霜,我报生活以浓酽的滋味,这或许便是生命最庄重、也最美好的应答。
- 第 1 版: 要闻 自治区十四届人大五次会议将于2026年2月2日在南宁召开
- 第 2 版: 生活经纬 “护娃神器”儿童电话手表真能放心护娃吗
- 第 3 版: 社会 从街头风景到千亿级市场 “新中式”服装扮靓“新消费”
- 第 4 版: 周末闲情 从一纸来信到民意回声